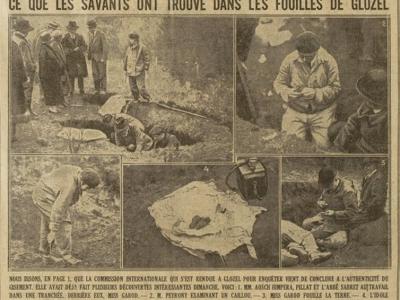科幻世界保卫战
乌托邦梦想
李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:“我也很热爱《科幻世界》。我也不希望《科幻世界》倒掉。”在被问到喜欢哪些科幻作家的时候,李昶列举出了刘慈欣、王晋康等人。当记者继续追问他最喜欢的科幻作品时,李昶长久沉默,之后说道:“科幻作品都是很好的嘛。”
“我们都很焦虑,我们希望有一位热爱科幻、懂科幻的社长带领我们走出困境。”
面对这一系列的“改革”,《科幻世界》资深文字编辑刘维佳说:“我们压抑太久了。”
“我想过离开,但我不知道除了科幻,我还能做什么。”刘维佳从1990年代开始看科幻,并尝试科幻写作,2001年进入《科幻世界》,一直工作至今。
在李昶上任的一年时间内,先后有4位编辑选择离开杂志社,却没有新人补充进来。“我们严重缺乏人手。现在美编只剩下一个人,译文版就剩下一个领导带着一个兵,现在都是拆东墙补西墙地忙。”
“李昶非常难以沟通,许多小编辑被他说得不敢再跟他争论。我们每次都要思前想后合计很久,才派一个人去跟他说。”一位编辑透露,李昶的口头禅就是,“没得必要,不讨论”。
《科幻世界》偏居西南,编辑的平均月工资只有1700元,即使如有10年从业经验的刘维佳,每个月也才有3000多元的收入。而去年一个新来的编辑拿着800元工资干了半年,其中每个月要花500多元租一间简陋的屋子,还要花200多块钱买书。
“这真的是一群固执的人,理想主义的人,不懂世故的人。要换了在别的单位和部门,大概都不会这样。”科幻作家韩松,熟悉《科幻世界》编辑部的运作。
曾经见证《科幻世界》创刊的69岁科幻作家刘兴诗说:“30多年来,在全国科幻界同仁支持下,《科幻世界》早已走向世界。从这个意义来讲,也是属于世界的,绝对不能成为任何私人的囊中物。”
许久没有在《科幻世界》上露面的科幻作家杨平,也出面支援编辑们。他对记者说:“其实,一位社长即使做过再违法的事,也不会导致今天的后果,编辑们和科幻迷们想要的很简单,请不要插手内容。他们只想要他们心目中的科幻。”
两个平行世界
“李昶上任后,《科幻世界》就分裂成了两个世界。” 《科幻世界》一位老员工说,“这次事件的整个过程是一次两个世界的对话,一个是理想主义的世界,一个是现实主义的世界。”
他认为,一方面,理想主义者无法理解现实主义者的世俗,另一方面,现实主义者认为理想主义者幼稚可笑。而这样的理想主义,自杨潇时代起,就在《科幻世界》杂志社成为一种精神主力。
杨潇1984年接手《科幻世界》的时候,它还只是一个“架空世界”。而这个瘦瘦小小的四川女人,就凭借着这样一股理想主义的力量将这本杂志带来了一个45万册销量的奇迹,开启了中国科幻一个新的时代。
“那个时候整个杂志的精神面貌非常不一样,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团体。”一名老员工说,杨潇非常有领导才能,能够调动每一个人的积极性,每个人可以直接向社长提意见,而这一点,在现在的年轻人身上仍然非常明显,他们热爱科幻,也听了很多创业者的故事,“他们把《科幻世界》当做延安圣地一样”。